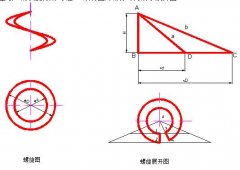走进绵竹年画村,迎面便撞上一片色彩的世界。青瓦白墙的川西民居外,一幅幅鲜艳的年画跃然墙上——执鞭的门神不怒自威,抱鲤的童子憨态可掬。游客们举着手机在画前流连,快门声此起彼伏。
近日,据了解,年画村目前正大力发展餐饮、民宿、特色农产品采摘及研学旅游,已逐步形成健全的产业生态。数据显示,2024年,年画村接待游客107万人次,实现旅游收入超4.2亿元;2025年上半年,年画村接待游客66万人次,实现旅游收入超2.3亿元。值得一提的是,年画还带动了村民的农闲时就业,人均年收入随之提高28290元。
尽管在文旅融合的助推下,绵竹年画得到了更多流量,但其仍有一定的产业瓶颈:一方面,受制于传统制作工艺,年画难以实现量产;另一方面,年画多用作伴手礼,其蕴藏的文化性和艺术性还未被充分体现,在定价上远不如时下的潮流文创产品。
绵竹年画村
年画“新生”:全国首个年画村成4A级景区
1998年的寒冬里,16岁的陈强裹着单薄的棉衣从外地回到绵竹老家。推开斑驳的木门,他看见四川电视台的摄像机正对着爷爷作画的手。而这位老人,就是日后被评为“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”“绵竹年画南派大师”的陈兴才。
镜头里,陈兴才握着鸳鸯笔的手稳如磐石,蘸着朱砂颜料的笔尖在宣纸上描摹出鲜艳的红色。“在家画画也能上电视?”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,在少年心里暗暗发芽。
当时的绵竹年画村还只是德阳孝德镇一个普通村落,大部分村民以务农为生。陈家人守着“传男不传女,传内不传外”的老规矩,在自家土坯房里制作门神、财神、童子等传统题材的年画像。陈强跟着爷爷学习“一黑二白三金黄,五颜六色穿衣裳”的制画口诀,用三十年树龄的梨木雕版印出墨线,再以矿物颜料层层渲染。
“最贵的‘群青’颜料要3000元一两,调色时需加入桃胶,冬日里还得用炭火保温防止凝固。”陈强对
年画颜料样品展示 “那时候年画就是过年赶集卖的东西,腊月里在市场上摆摊,赚钱贴补家用。”陈强回忆说。直到2003年夏天,河北画商通过媒体辗转找来,一口气订了200张年画。这笔大订单让他彻夜难眠,意识到“原来不过年也有人买年画”。
他后来才知道,这些画经过包装成为企业伴手礼,身价翻了几番。
随着越来越多主流媒体的宣传,绵竹年画开始声名远播。2006年,绵竹年画正式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。值得一提的是,与绵竹年画并称中国“四大年画”的天津杨柳青年画、江苏桃花坞年画、山东杨家埠年画,也在同期被列入首批国家非遗名录。
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左右。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后,陈强所在的村庄与另一个村庄合并,江苏援建方面希望将其打造为年画村景区。全国首个以“年画”命名的行政村就此诞生。此后,年画村在2011年成功获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
“年画村建成后,游客确实多了不少。”陈强回忆道,现在游客在参观景区时,自己会寻到工作室来。他边说边指着工作室外的小院,那里常有游客驻足观看画师们作画,也有游客进门亲身体验一番创作过程。
产业变迁:上半年文旅融合创收2.3亿元
在年画村的“农闲堂”里,一位来自成都的游客亲手体验了年画制作的全过程。她选择了一块雕刻着“哪吒闹海”的梨木版,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,用刷子蘸取墨汁均匀涂抹在雕版上,再将宣纸轻轻覆盖其上。
“要用这个拓包来回按压,力度要均匀。”工作人员一边示范一边讲解。
当宣纸被轻轻揭起,哪吒形象也跃然纸上。
还没完,后续的上色工序更需细心——等到墨迹完全风干后才能依次上色,且每一种颜色都需等待之前的颜色干透才能叠加。
这样的体验场景,在年画村已成为常态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农闲时,村里会组织当地村民聚集于此参与制作年画。“农闲时在家没事干,来画画一个月还能挣个2000元。”一位正专注为童子像上色的村民向
当地村民为年画上色 绵竹市孝德镇文旅发展中心负责人何艳青介绍,目前当地已构建起老中青三代传承人队伍,带动500余人从事年画相关产业。这是当地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有益实践。
此外,何艳青介绍,目前年画村已开发20多个系列的1000余种相关产品,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。同时,年画村正大力发展餐饮、民宿、特色农产品采摘及研学旅游项目,以形成健全的产业生态。她给出的数据显示,年画村20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66万人次,实现旅游收入超2.3亿元。
年画村景区的快速发展,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。从地图上看,年画村距绵竹市区7公里、德阳市23公里、成都市50公里,在“成都一小时经济圈”内,年画村还与三星堆、剑南老街等景点构成旅游环线。利用这些知名旅游景点引流,年画村成功承接了来自成都都市圈和三星堆文化旅游区的溢出客流,具备“文化打卡+民俗体验”的差异化旅游吸引力。
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璜分析说,当下文旅融合是重点发展方向,但在这个过程中,要警惕“非遗”的“活化”变成“异化”。他认为:“一方面,过度商业化导致‘非遗’失去文化本真属性;另一方面,‘非遗’产品的创新性不足,体验形式单一。这将导致非遗项目的同质化严重,缺乏独特吸引力。”
但在绵竹,还有更丰富的文旅项目。伴随中华年俗村等新项目的建设,这片土地正探索更多元的发展路径,让年画艺术在传承中探索更多可能。
价值突围:“非遗首先要让人吃饱饭”
在绵竹年画展示馆中,一幅格外引人注目。这幅中堂画作以财神赵公明为主角——他身披铠甲,手持金鞭,足踏黑虎,威风凛凛。
“这幅画完整展现了绵竹年画的五大工序。”绵竹市孝德镇文旅发展中心负责人何艳青介绍,它从设计、雕版、印线到上色、描金,全部由匠人手工完成。
据了解,年画村艺人们至今保持着传统的制作方式。用的是梨木雕刻版和矿物颜料。
年画村的画师工作室 “全手工制作是我们的特色,也是瓶颈。”陈强介绍,其工作室平均每个月接到的订单量在400~500幅之间,需要每天从早忙到晚。订单量大的时候,他也会聘请一些村民到工作室参与制作。
陈强算过一笔账:按照传统工艺完成一幅中堂画,从绘制到装裱配盒需要三四天时间,每幅画的材料和其他费用为100到200元。
“但现在我们只卖300元到400元,算上人力成本,这个价格并不贵。”陈强解释说,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定价,而是作为普通商品销售。
在陈强看来,制作年画的技艺门槛并不是太高,最难的是销售环节。据介绍,超过95%的客户需要他们自己寻找,剩下那5%的客户是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其他渠道主动找上门的。他透露,其工作室目前年销售额在50万~60万元。
相比之下,泡泡玛特等潮玩、热门影视剧或游戏周边产品的价格要比年画高得多。这种价格落差折射出非遗产品尚未突破“实用礼品”的定位局限,其承载的传统技艺价值与艺术内涵,在当代消费市场中仍未获得相应的价值认同。
因此,不少小型工作室仍在为销路发愁。陈强表示,近年来村里有不少年画传承人关闭工作室,选择去外地打工。“非遗首先要让人吃饱饭。年轻一代的传承意愿并不强烈。我女儿虽然会画,但以后要不要做这行,还得看市场。”陈强坦言。
仍有困局:为何说年画行业做文创难度大
但陈强认为:“年画很难效仿这些文创产品。文创是快消品,可能火一阵就过去了。对于年画来说,如果涉足文创,从设计到开模,投入太大,而且销售还没保障。个人工作室很难重投入。”
对这一困境,黄璜建议,年画产业可以探索建立“共享机制”,即探索设立共享制造工坊,集中采购原材料、共享高端设备,降低开模和生产成本。
对深挖年画的文化内涵,黄璜提出了几个建议:避免对图案的简单,讲好年画背后的故事和寓意,并将其与当代价值观结合;可以邀请用户共创作品,举办年画文创设计大赛,吸引年轻设计师和艺术院校学生参与,同时在社交媒体发起用户创意征集,让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。
对于产业的未来,陈强的观点是:首先要深耕年画背后的传统文化价值,比如将二十四孝这样的经典题材通过动画等现代形式重新演绎,让传统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被当代人接受;其次,迫切需要政府牵头搭建宣传推广平台,扩大年画的影响力;最后,需要多方构建稳定的销售渠道,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对接,真正解决手艺人的生存和发展困境。
陈强也发出了他的邀请:“这个行业没有恶意竞争,就算同一个题材,不同工作室或者画师做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。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传承人拿起画笔,只有百花齐放才能展现出年画的更多价值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