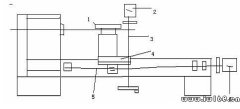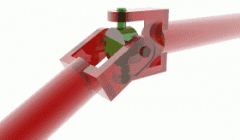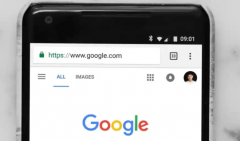她探访全球顶尖的农业大国美国时,发现干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。“曾经几十年,加州的农民一再刷新粮食收成与收益的纪录,全世界80%的杏仁产自这里。现在,持续的升温与干旱让农场主、城市和环保的水资源分配矛盾日益激烈,是否意味着加州丰富的农业资源耗尽只是个时间问题?” [3]
玛丽安娜·兰策特尔在此书中发出了上述疑问
1918年11月的某天,中国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。碰见梁漱溟,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。梁济问:“世界会好吗?”梁漱溟答: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
“世界会好吗?”每当极端事件发生时,总有人抛出同样的问题。近两个月里,高温不再只是天气概念,经由最切身的“酷暑折磨”和广泛的次生影响,其已成为所有人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。
过去很多年里,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渗入到了一些人更具体的生活。
日复一日的生态农业工作,让沈叶对生态修复有了信心。“你会发现人越遵循自然规律,就越少焦虑。环境可以让人变得不像人,也可以让人更像人。”
缓解气候变化,关键在于重新审视自然,尊重生态环境。农业也要用保护生态的方式种植,慢慢改良和保护土壤,恢复自然的农田生态。
沈叶依旧记得,通过生态培育,她和技术员把一块板结的土壤改造成了充满腐殖质的健康土壤时,那种无以言表的欣喜与感动。
正在研究土壤的技术人员
“土壤就像一只毛茸茸、有生命力的小动物。闻起来像雨后的空气,感觉很湿润,但又没那么湿。捧在手里,可以轻松捏成团,松开后它又能自然散开。透过土壤的孔隙,可以看到红色的小蚯蚓在蠕动。我当时又哭又笑,因为我真的发现土壤是有生命力的。”
牧民的智慧:梵文说给鼠兔听
严峻的图景,凸显出通过大规模减排控制升温的紧迫性,所幸的是,人类社会对此的共识正在不断凝聚。
张学斌回忆起他参与编写IPCC时的经历,2018年报告发布后,当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反应平平,甚至还有人反对报告的结论。
而在2021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,AR6报告的内容已经被当作事实肯定下来,成为政策讨论的科学基础。
“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,是很大的进步。到了现在这个阶段,假如再不把科学当回事,那我们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”张学斌在电线月,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吟隆,在B站上分享了一场“关于农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”的讲座。在他看来,对双碳目标 ,需要智慧性地实现。“除了减缓,我们还要适应气候变化。”
像这样的报告,许吟隆一年要做几十次,但他仍然愿意反复讲,目的就是呼吁大家加强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。“现在的环境也在逐渐变好,大家也在逐渐认识到适应的重要性。”
如何适应气候变化,冯启华切入的角度是可持续农业。
在田间地头研究可持续农业的冯启华
“每当气候变化时,农业的收成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作物的韧劲。”冯启华表示,多元化种植、使用适应当地的老种子,虽然产量不是特别高,但对抗极端天气的韧性更强,这种方式也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探索。
为缓解草原退化,泽昂甲感触最深的是“牧民的智慧”。
牧民种草不是简单地把草籽撒在土地上就完了。他们把草种在坡度比较高的地方,横着种,起到不被暴雨冲走的效果。“种子不能埋得太深,只要不被鸟吃走的程度就可以了。撒完草籽,把牛牵过来,让牛踩土地,把草籽踩进地里,同时也起到固土的作用。然后接下来一周的晚上,都把牛赶过来,牛的粪便形成草籽生长需要的天然肥料。”泽昂甲说。
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,牧民们每天需要较量的是鼠兔对草原的破坏。鼠兔的数量连年激增,它们吃草很厉害,还会在地下打很多洞,这些洞在地底连成网,土质变得空心。
“牧民们把新种的草原围起来,在边界上放一个旗子,旗子上写着古梵文。”说到这里,泽昂甲顿了顿,“你有兴趣听吗?这可能听上去不够科学。”
众生平等,尊重自然,飘散在青藏高原上写给鼠兔的那些古梵文,何尝不是对人类的谆谆告诫。
泽昂甲谦虚地说,自己的普通话还不够好,对气候变化的理论水平不高,认识也是参加了“自然之友·玲珑计划”后才了解到。但我却觉得,他对气候变化的理解非常深刻。
他说,气候是一个生命呼吸的
气候是大自然中覆盖面积最广的,也是所有生命依赖性最高的,它可不就是如同呼吸吗?
如果不是因为今年的异常高温、能源紧张,习惯了城市生活,夏天一热就把空调开很低的我,怎么也不会关注到高温以及高温背后的严峻生态状况。我们几位
但和泽昂甲、冯启华、沈叶聊完后,我们又不焦虑了,他们扎根生态保护一线,对问题感受真切,却仍保持积极乐观。他们的乐观在于每一天的付出。保护生态,原来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了。
行动刻不容缓,但更需要智慧。就像泽昂甲所说的那句藏族俗话,“无行动的智者像无武器的英雄,无智的行动像宝剑落入疯子手中”。无论我们是科学家、媒体人、生态保护者,还是普通公众,多学一点生态常识、多做一点生态保护。有果必有因,反之亦然。勤耕耘者,欢喜收获。
[1] ,央视新闻
[2] 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21年9月版